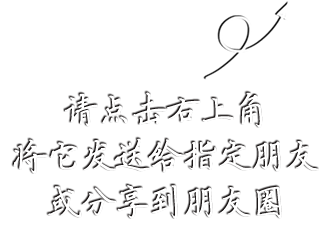编者按
在洞头,有许多致力于研究闽瓯文化和洞头本土文化及史料的学者、文人和爱好者,他们通过大量阅读相关书籍记载和实地走访,颇有收获。本报特开设《一家之言》专栏,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有趣观点。这些文章内容仅代表研究者个人观点,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或来电参与讨论。
吴逢旭/文
历经数百年风雨冲刷和巨浪冲击的一批“古海塘”,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潮中终结,实为文物保护领域的一件憾事。
本文所叙之“洞头古海塘”,包含了《洞头县志》记录在册的兴建于康熙三年(1664年)的“小长坑塘”,兴建于嘉庆二十四年(1856年)前后的“埭口塘”和“仁前涂塘”,兴建于光绪六年前后(1880)的“黄岙塘”。近二十年来,洞头加速城市化步伐,这些古建筑如今也仅留一丝遗存。笔者认为,这些兴建于清初,代表着第一批从福建沿海或者温州平原迁徙到百岛的洞头先民,凭借着“改天换地”“移山填海”的顽强意志,为后世子孙的繁衍昌盛而兴建起来的“民生工程”“良心工程”,仍留存人们的心间,并未随着时间而烟消云散。
那么,这些“民生工程”“良心工程”究竟有哪些“价值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缅怀?
良心工程
护佑一方百姓,兴起一批村居
海塘历来有“官塘”与“民塘”之分,“官塘”类似于今天的“国家重点工程”,朝廷拨款、指定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并摊派民工,建造过程载入史籍。(1)而“民塘”纯粹为民生需要、民间发起、民众施工。有人做过统计,在温州历史上,能够列入“官塘”的,仅有一处。
建于清代的上述洞头四处“古海塘”,正是明末战乱、清初“海禁”、清中期平原地区人多地少矛盾激烈震荡的情况下,“入岛求生”的先民兴建起来的4处“民塘”。
“民塘”的身份在各种官修的史书里鲜有记载,有的可能只在宗谱里留下一笔。至于发起人是谁,何时动工,资金如何筹措,多少民工参与,动用怎样的建筑工具,石料来自何处,期间被海潮冲毁了几次,是否有朝廷派人前来巡查,何时竣工等等大事要事,多数未详。
我们只能在温州大陆同类海塘中,找到相应的“参考资料”:
——关于资金来源。《弘治温州府志》记录了平阳县万全乡修建海塘是“乡民”林居雅“变卖全部家产”作为启动资金;有的是各乡村大户人家共同集资兴建;有的甚至请僧人四处化缘求得。据《洞头县志》记载,“小长坑塘”是柯氏族人围垦,围地60亩;“埭口塘”最早是平阳矾山(今苍南)人围建,后苏氏族人变卖田地后加高加固,围地540亩;“仁前涂塘”则是18户村民自发组织围筑,围地100亩。这些都符合“民间发起”的特征。
在洞头百岛上崛起的这些古海塘,为迁徙到此的先民提供了立足之地,稳定了人心,也为岛上生产力的快速集聚,提供条件。
捍海护田 历经数百年不倒
既是“良心工程”,就不存在层层转包、偷工减料,以次充好、“豆腐渣”遍地等等“潜规则”。前人总结海塘的两大功能一为“捍海”——实际上就是围海造地;二为“蓄流”——能够蓄积、分流上游来水,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便利。
那么,在200年至300年前的洞头偏僻海岛,先人用什么样的技术,造就巍然耸立于海面(即坝高)3—5米的水利工程?
仍然要参考文人叙事。
一是今人叙事。据《洞头县志》记载,洞头第一塘“小长坑塘”的建造技术为:“石头护坡”“海泥闭气”,彰显“科学精神”。洞头的其他几处古塘一概采用这种技术,这中间是否有相互借鉴或模仿未可知也。
二是文人叙事。明代举人、平阳万全人蔡芳在《平阳万全海堤记》一文中记录了繁杂、精准的修筑技术:用90公分的长条石为“经”,60公分的短条石为纬”“纵横积叠,上下参错,复以乱石杂土,傅其里以为贴帮”,文中提到“杂土”,是不是指“用来闭气的坚硬海泥”,未详。(2)但也显示出先人严谨科学、就地取材的高超智慧和对子孙后代负责到底的担当精神。
三是发掘发现。显然,“官塘”的建造则奢豪、极致。最近考古发现,与大运河、万里长城并称古代三大建筑工程的“钱塘古海塘”,采用“丁砌”和“顺砌”(建筑用语)的方法筑坝,石头缝隙间用糯米汤、石灰等灌注,其坚固程度优于现代水泥。堤坝下还有鱼鳞一样铺排的块状巨石,堤坝再采用阶梯状向上延伸,能将滚滚巨浪化为温顺的海水。据称,“钱塘古海塘”每公里要投入2000名建造工人、耗费黄金300两,总长度306公里的海塘,投入巨大,可见保护杭州湾大粮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被城市化浪潮冲毁
不是一件幸事
关于洞头的海岛开发,历来缺少“不可移动文物”。
为“五岛连桥”精神之先驱的洞头古海塘,在浙江乃至全国的版图上,有着独一无二的遗产价值:“石头护坡、海泥闭气”是否洞头首创,值得考证;民间集资、蚂蚁搬家的“愚公移山”精神实乃海上丰碑,值得礼赞;去年,杭州九堡建起了国内第一座“海塘博物馆”,并称要积极申遗。洞头在建设“海上花园”的伟大征程中,“古海塘”的旅游作用和文物价值不能缺席,值得我们去思考、深挖和保护。
参考文献:
1、《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、塘河的形成》,吴松弟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7年第1期。
2、《温州海塘遗产的文化意义》,刘小方,《温州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1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