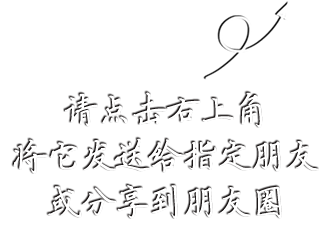黄忠波/文
离开家乡已近三十载,每当想起那儿时的情景,幕幕都在脑中显现。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带着儿孙们回到故乡过年,到处走走看看,那石阶、石墙、石房,整个村庄几乎是清一色的石头垒成;那海滩上的鹅卵石似乎还是那么烫脚,看着岸边垂钓的人们,仿佛我又回到了从前;房前的老槐树还是那么茂盛青翠,往事历历魂牵梦绕,难以割离。
我的家乡在霓屿下郎村,它地处霓屿岛西南方,进入瓯江口的船只需经霓屿岛南侧海道,在船上向岛上观望,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悬空挂在山壁上,石头民房依山而建,层层叠叠相互交错,乍一看就像岛上的一座阁楼,因此它又有一个别称为“海阁古渔村”。
老家的民房是建在岩石上的,地基是从岩缝里凿出来的,建房的石头就地取材,挖地基的石头成了建材,省工、省钱、省时,因此下郎村一溜烟都是石头房。整村有五行三纵,每行都有十几间民房,每栋房子间隔不到一米,上下行之间高差都在七八米,所以每行房子前要堡坎,房后也要堡坎,每间民房前都有围栏,三条古道分东、西、中贯穿全村,人们在村中纵向走时就像爬楼梯,坡度约70以上,村民们运送货物和渔具都靠肩挑背扛,可见地势的陡峭和出行的不便,有副对联是对下郎村容村貌的真实写照“层层叠叠纵横交错悬空壁,垒垒砌砌竖直撇捺成一阁”。为何先人将房子建在陡崖上,听说是为了防海盗,盗贼来了可从山上滚下岩石驱走他们。
老家的民房是历史延续的见证,可以说是海岛民宅建筑的博物馆。有一民房至今已有两百多年,本是单层三间门面两厢房,可惜右厢房已拆建,左厢房保留着,据说黄氏三房曾祖在此房里生了九个儿子一个女儿,因此该房也称之为“九子房”。还有清末民初的筒子房(老百姓叫“竹高笼”)、五十年代的“粽包房”,其各式是房顶中间隆起,然后向四方延伸出檐,形如粽子、六十年代的石瓦房,四方端正,分上下两层、七十年代的石砖混合,即上层砌砖下层砌石、八十年代为挑廊房,其二楼屋檐往外挑形成走廊、九十年代的钢混高层民房(三层以上),现在已是别墅满山。
我的家乡是解放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霓屿南片的经济文化中心,当时霓屿乡政府在桐岙(以前叫东岙)。计划经济时代,群众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物资都在供销社进行交易,霓屿设两个点,一个在桐岙,一个在下郎,每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,后来下郎滩头增设供煤点,除村民们背筐挑担卖煤,海上船只更是来往如梭。那时霓屿诊所也分南北两所,霓南六十年代设在汪头,七十年代末搬到下郎,下郎成了群众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心,现在供销社已成过去旧事,医院也迁到正岙,但其建筑还保存完好。
孩时的滩头是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霓屿渔业张网基地,岙口的海面上就是下桩张网的好地方,船只从海上网地起网回到岸边来回也只有个把小时。五六十年代用的是单帆舢舨(当时称“长七五”意思是指船长一丈七尺五),岙口网船有几十只,除本地外还有乐清、永强等地的渔民,岙里和两边的山坡上搭了几十间棚房(也叫棚场),一只网船一间棚场。一出海风帆点点,螺号声声,船只凭风驶向网地,回到滩头人声鼎沸,抬渔货的、遴选鱼虾的、各间棚场炊烟四起忙着热蒸红虾,而后晾晒在竹篾毯上和山坡空地上,远远望去一片通红,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海鲜味。一到夜晚煤气灯盏盏亮起,照亮了海滩和山坡,形同白昼,宛如城里的夜市一般。
以前孩子们最爱到滩头,浅浅的海湾是天然的游乐场,夏天一到,两百多米长滩上的鹅卵石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,大家争先恐后扑向大海,游得欢畅,玩得开心。水涨船高岸边又是垂钓的好地方,大家将海蜇花、红虾做诱饵,上钩的都是黄鲷和鲈鱼。趁大人休息时孩子们爬上舢舨,扯上风帆在岙口驰骋一番,惹得大人们高声训斥,大伙一哄而散,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我家房前有棵百多年的古榆,一年四季常青,十分茂盛,新叶抽齐才落旧叶。夏秋时节大树是鸟雀的天堂,天稍亮树上鸟儿已是盛会召开,上下翻飞叽叽喳喳闹得大家不得不起床,在轻如薄纱的朦胧晨雾中村里家家户户冒起了炊烟,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一到傍晚鸟雀们更是高歌争胜,清脆的声音响彻全村。等月亮星星挂上树梢,鸟儿歇息了。然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和孩子们聚集在树下休憩、听老人们讲故事。孩子们一边听故事,一边躺在石板上数星星看月亮,憧憬那美好的明天。
沿村中台阶上到村子顶端,远视可面向大海将洞头、大小瞿岛、南宁、冬瓜屿、凤凰山岛尽收眼底。朝向岙口海上是千亩紫菜牧场,那一条条如栅栏、一排排似铁轨、一块块像田园,尤其是那白色的塑料浮筒宛如是珍珠撒在玉盘上,十分的壮观。
忆往昔看今朝,家可离情难忘,家乡的蜕变令人欣慰,一群孩子围上我说:老爷爷您看什么?我领着他们指向山、看着村、望着海、对着房说一切都变了……如诗如画如梦。